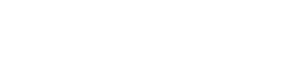第27节(1/2)
作品:《沽酒[虐恋]》
不住疲累。
“我没事,无需担忧。”他凝气探向气海,松苓设下的那层罩子起了裂痕,竹韵霸道的真气紧紧扒在上面,过了一日由于,竟还没泄了去。
“醒了啊。”竹韵面上不显,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。
淙舟颔首,轻声道:“劳烦挂心。”
竹韵心心头像是被人一捏,他顿感不顺,虽说往日淙舟也是对谁都客气,可却从未有过这样的疏离,自打重逢,淙舟总是这样的疏离。
“哥哥…”松苓见人醒来,才敢开口。
泪终是滑了下来,在人手背上迸裂。这日哭的太多,眼睛有些疼,可他实在是害怕,淙舟出一点事他都不愿,他再也等不起下一个百年,实在太长了些。
沉疴百年,终生难愈。
“守我一夜,不困吗?”淙舟抽出手,将松苓鬓边凌乱的发别到耳后。
“困啊,”松苓握着他的手,阖眸蹭了蹭,“哥哥醒不来,我怎么敢睡?又怎么睡得着?”
淙舟轻笑,撑起身挪出半张床,拍了拍床板,道:“上来睡。”
那边竹韵被人忽略的彻底,猛的吹了口气将蜡烛吹熄。
昏黄没于天光,屋内暗了不少,松苓抬眸看了一眼竹韵,接着越过淙舟,钻进床里,藏在被中脱去衣裳,一头扎在淙舟颈窝不动了。
竹韵再也待不下去,他瞧着松苓瞥他一眼,那眼神就像抢了人丈夫花坊姑娘。
“你没事了我就走了,”他抬手褪去结界,攀窗而来又攀窗去,“你们什么时候动身,记得叫我一声。”
“好。”淙舟应了一声,依旧疏离。
窗扇开合,进了一缕潮湿的风。
骤然静谧,只是那扇窗还破着,不需片刻,地上便积了一滩水,呼呼风声吹的人难眠,松苓爬起身布下结界,又将床帐子放了下来。
不闻声响,不见光亮,松苓窝在人怀里,狐耳轻轻摇晃。
“你梦见什么了?”他轻飘飘的开口,显然睡意已浓。
“不记得了,”淙舟被那耳朵扫的痒,抬手压了压,“只记得周围黑麻麻一片,似乎有一座山,其余的都不记得了。”
“嗯…”松苓翻了个身,尾巴搭在淙舟身上,抱着人手臂,将要入睡,“那就算了…好困好困…醒了…醒了再说吧…”
“嗯,”淙舟轻揉着一根狐尾,“醒了再说。”
他不曾妄言,确实记不得。
——
风携落叶吹过窗棂,落叶留在菱格中。松苓像是被淙舟吓的,未至半月已好了大半,待他好全,已然过了暑天。
且说那白尾鹫,整日盘旋在云间,夜深人静时才敢悄悄落地,只是这两人几乎不出房门,整日腻在一起说着小话,它实在没有可传之言,那些个小话它听的直掉毛。
启程这日,松苓并不想带着竹韵一起,奈何这人长了个狗鼻子,嗅着味道跟了过来。
竹韵今儿个配了剑,剑鞘墨染,衬着银边,那股子戾气显得更重。他看着淙舟怀里的狐狸,这人也是懒得要命,不是没有腿,偏要人抱。
“你俩就打算走着去?”他见淙舟挎上行囊,不待天明就往城门走,一把将人拉住,“这得走到什么时候?”
淙舟闻声停下脚步,他从没考虑过这件事,自他醒来松苓就在他身旁,他抱着狐狸从北走到南,走走停停一直如此,故而此去涂山,他也不曾想过要如何去。
就连松苓也是闻之一愣,显然他也不曾想过。他脱出淙舟怀抱,赤脚落地,一袭赤红广袖衣衫,衬得人白。
松苓顺手接过行囊往袖中一塞,那鼓囊囊的包袱也不知去了何处,大袖飘飞,如红叶积坠。
“好问题,”他摸着下巴,偏头看向淙舟,“要不我驼你去?”
人太过夺目,红衣穿不得。
淙舟收回目光,问道:“你如何驼我?”
“我化原身便可驼你去,”松苓不觉有异,兀自说道,“那城不过七百里远,片刻就到,既是疫病,便拖不得。”
“你化原身怕不是要吓死人,”竹韵呛声道,“赶明儿就得传来流言,说九尾狐再度现世,天下将乱。”
真是句句捡着人不爱听的说,刀子一把把的往人心窝子上捅。松苓闻言怒火骤生,后槽牙近乎要磨碎,若不是淙舟还在,他早已咬上人脖颈。
“那净泽君说说,怎么去?”他没什么好脾气,“哥哥现在御不得剑,你们嵛山法器颇多,怎的不想个法子?不若弄
第27节(1/2),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