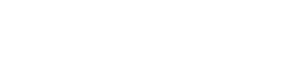第26节(1/2)
作品:《沽酒[虐恋]》
淙舟不曾插话,只揉着狐狸后颈,将那一身炸起的毛揉顺,卸了脾气。
“那是我的,”松苓被揉的舒服,声音瞬间软了下来,甚至带了些撒娇的意味,“哥哥挑的线,我打的璎珞,净泽君无情无爱,哪懂得这些。”
这话可真是戳人心窝子,再听着松苓这语气,竹韵只觉脑袋疼,他捏着茶盏,耳边响起细小的碎瓷声,茶水洇了出来,裂在衣袍上。
“我不与你辩这些,我今儿个来是有正事,”他换了个茶盏,又饮了一口茶,“师兄要去涂山,我与师兄同去。”
窗纸哗响,这时候也不好叫小二上来,淙舟拽过寝被将松苓裹住,松苓攀着他胳膊,顺势枕在人膝头。
“你去做什么?”松苓猛的紧攥住淙舟的衣袍,眸光不善,“你们般若岩上的人还敢往涂山去?哪来的脸?”
竹韵轻笑一声,抬眸看了看淙舟,那人像是当他不存在,只垂眸瞧着松苓的发顶,揉着那只轻晃的耳朵。
雨打湿窗纸,外面雨势渐起,风穿过裂痕灭了床前的烛。
“哥哥,”松苓借着黑暗,把脸埋进人下腹,“困了。”
淙舟似是笑了一声,他怕人受凉,将人裹好,侧目看了看一旁的竹韵,那人竟还坐得住。
“睡吧。”他轻拍松苓后背。
竹韵长叹,抬手布下结界阻挡了风,接着一个响指点亮烛台,青虚虚结界下烛火亮的突兀,松苓抬眼一瞧,心道这色同长离的极像。
“你干嘛,”松苓不悦,指尖绕着淙舟的发,“觉都不让人睡吗?”
“正事还没说完睡什么觉,”竹韵也觉得不爽,周身戾气环绕,他侧过身去,抱臂倚靠着桌案,“我不去涂山,不过是与你们同行一段,东行七百里有城犯了鼠患,接着起了疫病,师尊叫我去看看。”
听了这话松苓不禁嗤笑,他缓缓翻身,仰躺在淙舟腿上:“你们那个神尊,”他伸了个懒腰,“神尊不是闭关吗?怎的又知晓西南的疫病?”
“师尊通晓八方事,自然是看得见,况且各个城中皆有我嵛山设下的高塔,此等疫病,也该让师尊知晓。”竹韵回身端起茶盏,白瓷轻碰。
“这次又要…”
“那座塔叫什么?”淙舟倏然询问,打断了松苓的话,他不知竹韵怎的点燃了狐狸的引信,只觉的人要炸。他依旧轻拍着松苓后背,示以安抚。
竹韵摇摇头,他道:“没有名字,就是一座高塔,各个城有各个城的叫法,瞭望塔,瞭望楼,检察署,叫的花样可多。”
他似乎很渴,仰头饮尽杯中茶,这茶是糙茶,竹韵喝不惯,却又斟了一杯,像是今夜要去淙舟彻夜长谈。
淙舟没再问其他,房内蓦地陷入寂静。
“这次这疫病,”松苓冷笑,直楞的看着覆了一层结界的窗,“这次的疫病嵛山要又要如何处理?是又寻着了哪儿的良药?是活物还是死物?若是医不好,又要怪在谁的头上?”
松苓双目晦暗,盯着窗,颇为空洞,接着眼圈倏然泛红,一颗清泪滑入鬓发,他一眨不眨,任泪流入发间。
没有呜咽,不闻抽泣,只有大颗的珠子像是脱了线,落得比窗外的雨还要急,那些回忆像是决了堤,顺着泪一同涌出。
记忆中的景象与方才的梦境混淆,松苓起了一瞬的幻觉,只觉那扇窗外有无数血手攀附,叫嚣着要把他拽进无边血海。
松苓要喘不上气了,他猛的一抖,一只微凉的手覆上他双眼。
“不想了,”淙舟擦去湿润,只留下一双湿亮的眸子,“听话,睡觉了。”
他说的很轻,轻到只散在帷幔里,落进松苓的耳朵。竹韵不曾听清,他拨着茶盏子里的仅有的几片茶叶,茶水烫手,可闻得裂釉声。
“师兄也是般若岩上的人,”他冷不丁的开口,“他去涂山你怎的不拦?”
一支枕头骤然飞来,竹韵没能接住,枕头打翻了茶盏,玄袍上霎时多了一片茗烟。他被烫的抽了一口气,搁下茶盏,掀开袍摆,扭头瞪向松苓。
松苓也瞪着他,那样子像是要把他撕碎。
“鸣沧君叛出师门,这可是你的好师尊亲口说的,”松苓一手支在淙舟腿上,撑着上身,言辞激烈,“般若岩上已除他名,怎能还算做嵛山人?”
竹韵正了身,他像是没有脊骨一样歪在桌案上,望着那凌乱的床铺,眸光落在床边的白玉上,他道:“可师兄腰牌还在,师尊那是气急了,他可是一直等着师兄回家。”
“你们师尊
第26节(1/2),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