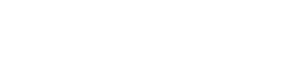第56节(1/2)
作品:《欺世盗命[HE]》
情捡起靠在柱边的拨火棍,一瘸一拐地跟上她,口里仍旧喋喋不休:
“不过呐,我瞧那妇人盼子心切,磕头时额上都磕出了血,看着是真想同她那夫君留下昆裔。是不是师父不曾食过人间烟火,不晓得她的急切心思?”
天穿道长倏然止步。夕晖宛若轻纱,笼在她素丽的面上。她忽而道:
“我有孩儿的。”
易情瞪大了眼,目光不自觉地流连向她平坦的小腹,那儿何时孕育过一个生命?天穿道长却戛然掐灭了话头,不再言语,踩着石阶向下行去。易情怔了半晌,连支着身子的拨火棍也抛了,趔趄着赶上前去,叫道,“不是罢,喂,师父,你甚么时候有家室的呀!”
他还是个小孩儿的时候,就屁颠屁颠地跟在天穿道长身后。天穿道长将泥猴儿似的他捡回,带他在天坛山上犁田、浇菜、摸鱼捉虾子、画道符,天穿道长就像他的一片天,像他的生母。
“呃…师父,您的那位……师娘,不对不对,是您那口子,究竟是谁呀?我怎地不曾见过?”易情小心翼翼地问道。
天穿道长闭口不言,神色冷肃如坚冰,快步从他身边行过。
“师父,您就告诉我罢!”
白衣女子冷冰冰地道:“没那个人。”
“那您的孩儿呢?”
“死了。”
易情说:“噢……您,您节哀。”他隐约觉得,天穿道长似是有许多事不愿同他叙说,关于这人世之事,还有她的往事,这些秘辛皆蒙尘在她心底。
正神游天外时,他却见天穿道长在石阶上驻足,回过身来。她的神情依然是澹泊的,远山眉舒扬开来,道:“说起来,你今日到这月老殿中寻我,是为了治头痛一事罢?”
她不提此事倒好,一说起这事,先前被极力抑下的头痛忽又如潮袭来,犹如惊雷般在头脑中炸开。易情冷汗涔涔,禁不住弯下身子,扶着脑袋呻吟起来。
那痛楚是自魂神中降下的痛苦,浑身都似被利刃劈开。无数幢幢鬼影在眼前盘萦,世界仿佛裂成无数星屑,在面前飞舞盘旋。
在无边的痛楚之间,他落入了一个暖热的怀抱。
易情竭力抬眼,却见天穿道长不知何时已回过身来,将他拥在怀里。
素色的系带上以银线绣着曲绽的槐花,绸衫上似飘来白梅、牡丹蕊末研成的冷香。易情觉得自己像被一块寒冰相拥,但这块冰却温暖如春。
白衣女子闭着眼,轻声哼起小曲,缓缓地摩挲着易情的头。那似是娘亲给襁褓中的婴孩哼唱的软调,像丝绸般滑过耳畔,落入心底。
奇的是,易情的头痛似是减轻了几分。
他心里忽而涌起一股难言的酸涩,仿佛许久以前,也有人向他唱起如此一支柔软的歌谣。
突然间,天穿道长放开了他,温暖消失了。
“头痛好些了么?”她问道,神色冰冷如初,仿佛方才的温柔不曾有过。
易情木然地点头。
天穿道长冷淡地道:“那就成,若是还痛,你就自己看着办罢。”
说罢,她便一拂白袖,头也不回地往石阶下去了。
第三十九章 杀意何纷纷
茅顶上有一个破洞。
破洞里是一片如帕子般小小的天穹,时而透出明净的星蓝,时而是墨色的漆黑,风和雨会于其间悄然钻落。养伤的时日里,易情闲得无事,便会仰头瞧看。缥缈的云彩之上藏着绚丽辉煌的紫宫,而他却只能卧在九重天之下的一蓬茅草间,百无聊赖地远眺。
他本该静养,却总挨观中众人指使折腾,天穿道长常唤他去月老殿中帮女客们画红线,微言道人又揪他去以血画法箓。于是他胸前的剑伤仍旧血肉模糊,头痛也时好时坏。
起先微言道人还给他送过几瓢疗伤金津,后来竟似将他抛至九霄云外,忘了个干净,再也不曾造访过他这寒舍,天穿道长更不会来主动探访。他行出茅屋门,时常觉得四周清寂,杳无人烟,眼前尽是茫茫白雾与迷蒙的云水,没有尽头。
虽是夏时,可入了夜,天坛山中便会寒冻难耐。易情冷得辗转反侧,索性爬起来,支着拨火棍去寻三足乌。这鸟儿自称是太阳里的赤乌,抱起来确也如手炉般温暖。易情捡到它的那段时日里,他俩常裹在破蒲席里依偎着入眠,如今少了它,夜里更为难捱。
黑漆漆的松林里,只有飞旋如星的萤火与他一路相伴。易情寻遍了无为观,最终在玉兔的寮房里寻见了它。寝寮灯烛荧煌,映得幽林犹如白昼
第56节(1/2),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