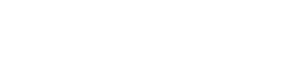第3节(1/2)
作品:《沽酒[虐恋]》
不能再想了,心脏像是滚过细密的针,没有那么疼,却也疼,疼的磨人,疼的全身都麻。
夜更深了,树梢微弯,簌簌树叶交替掠过月光,狐狸轻声嘤咛,蜷身窝进仙君肘弯,秋日还未至的凉意顺着风穿透皮毛,和着心尖的针直直透骨,它在南风中打着抖。
淙舟垂首看着狐狸,狐狸抖的可怜,叫人心生疼惜,他抬袖将狐狸盖住:“才至夏末,你便觉得冷了吗?”
狐狸又是一声嘤咛。
淙舟从未见过狐狸如此模样,平日里只要不上房揭瓦,他都觉得已是万幸,猛见狐狸如此,淙舟心里倏然一软,倒也不能说是养不熟。
他半拢着狐狸,随妇人回了小院,晚风带来远处湖泊里的潮气,将小院浸的阴气更盛。山野木屋不便沐浴,淙舟打算和衣歇息一夜,他总是睡的很沉,就连呼吸声都几不可闻。
狐狸钻出他的怀,四爪轻点床榻,缓步至淙舟颈侧,它露出犬牙,蹭过淙舟脖颈,接着张开口,牙尖抵住皮肉,狐狸犬牙锋利,只消稍稍用力便可见热血奔涌。狐狸使了些劲,犬牙刺破皮肉,它舔到一丝血腥,倏然收了口。
狐狸还是心软,它下不了这个手。
它轻轻舔着那细微的血,神色哀伤,喉中不断发出轻细的呜咽。淙舟似是听得,抬臂将狐狸搂进怀中,却又不曾醒,呼吸依旧微弱,就连狐狸的赤毛都鲜有波动。
屋里未关窗,月光落在床榻,狐狸浴在一片银白中,悄然化作人形。他不着片缕,墨发铺散,发间的耳朵未曾收回,身后垂着六条尾巴。
狐狸翻了个身,下巴垫在淙舟胸膛上,抬手拂过淙舟面颊,他指甲有些长,淙舟许久不曾为他修剪过了。
淙舟似有所觉,环住了狐狸后腰,鼻息不断落于胸前,扰的人有些痒:“别闹,”他将狐狸扒下胸膛摆正,紧箍在臂弯里,“快睡。”
这动作未免太过熟了些。
月亮好亮,哪怕是隔着窗都照的人眼疼,狐狸掩着双眸,一条尾巴卷在人身上,唇角牵出一丝苦笑。
杀吗?舍不得。
走吗?不太想。
千滋百味快要将他扯碎了,这情滋味啊,着实难尝。
“你再叫我崽子我一定咬死你,”狐狸故作咬牙切齿,言辞间却透出哽咽,“我叫松苓,松苓酒的松苓。”
他回身枕在淙舟肩窝,尾巴耷在身后,垂落床沿,像是久不见甘霖的花木,有些蔫,有些…不开心。
翌日清晨,淙舟睁眼时狐狸早已不在,右肩有些疼,手臂有些麻。他稍缓了一会,撑起身时扯到了脖颈上的伤,这事隔上几日便要上演一次,狐狸似是想吃了他,又似不想,淙舟习惯了,不算疼。
淙舟铺好床褥,推开门欲寻狐狸,却见狐狸背身蹲坐在门槛上,正舔着爪子为自己理毛,浴在日里的毛红如秋枫,尾巴支棱在晨风中,像是怕扫到地上的尘。
讲究的狐狸。
淙舟展出一个不明显的笑,上前将狐狸抱起来。松苓在他怀里打了个滚,微微张嘴,淙舟瞧见了它牙尖残余的血。
“这是偷了谁家的鸡?”淙舟自言问着,今儿心情莫名舒畅,言语中都带着难得的轻快。
松苓闻言不悦,这人醒着的时候从来不会好好说话,不是叫他崽子要当他爹,就是冤枉它偷鸡。松苓喉中滚过一声低吼,叼着淙舟的前襟就往院子里拽,淙舟抬脚踏出庭院,只见稚儿正熟练的杀鸡放血。
再往远了看,便可越过院门,看见那一座座的坟包。
稚儿手中握着一把砍骨刀,那刀又大又重,可那稚儿却寻了个好方法,他将砍骨刀嵌在木桩里,腿间夹着整只山鸡,一手握着鸡头,脖子悬空着往砍骨刀上凑。山鸡都来不及叫上一声,便被抹了脖子放了血。
稚儿脚边躺着四只死鸡,手里的是最后一只。
“神仙哥哥醒了?”稚儿拎着鸡起身,身上的粗布围裙沾满了血,这事他做惯了,对身上的血腥浑然不觉,“小狐狸起的好早,我起床的时候天还没亮呢,小狐狸已经叼着山鸡回来了,它可棒了。”
虽说是被一个孩子夸,但松苓还是很开心,他并非起得早,而是为了这几只山鸡一夜未眠,他现在好困,眼都要睁不开了,但还是用鼻尖轻轻碰了碰淙舟的胸膛,一副讨赏的神情。
淙舟抬指轻挠狐狸下巴,算是奖赏。
“娘说今天炖两只鸡,一只给爹补补身子,一只用来答谢仙君,”稚儿垂眸间终是发现了身上脏污,微微后退一步,不叫身上的血
第3节(1/2),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