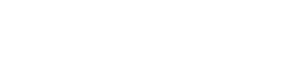第60节(1/2)
作品:《疯子酒[互攻]》
的动作,就算从生疏到熟练只用了两三天,她也从未停止过自我谴责。
她没有资本再去荒废功力了,再这样下去,她身体里的角色就要与她剥离——找不到犯花的那几天里,她是这样想的。
可这次好像有些不一样了,直到出发去晏城的那天,她还没有找回原来的状态。
《弦断声》里有一个情节,是张军把情绪濒临崩溃的犯花拥在怀里,犯花拼命地捶打他想要挣脱。背景音逐渐消失,灯光只剩下他们头顶的一盏,犯花的无力就在这中间传达出来。
排练的时候,宋辞一如往常地被李成河圈进怀里,她抓狂又呐喊,用力地颤抖、把自己缩成一团。一切好像都在稳步进行着,她却突然间停了下来。
她静下来,呆呆地挂在李成河身上。犯花的无力变成宋辞的无力。
李成河明白发生了什么,他也一动不动地站着。或许宋辞只是需要缓过来的时间,他想,或许理解犯花真的太难。
“张军……”宋辞顿在这里,摇摇头重新开口道,“李成河,我好像找不到她了。”
她所有的肢体语言都在,所有的记忆和动作,甚至给旁人完全看不出区别来。只有她自己知道,那不是犯花在跳。
之前怪罪到疏于练习上,后来觉得是没进入场景,和李成河搭着跳到一半多了她才终于接受这件事——她好像真的找不到犯花了。
机械的、并不真正因绝望而生的颤抖,她装不下去了。
半晌,李成河安慰她道:“也正常。”
宋辞不答话,她明白事情已经脱离了自己的控制,事到如今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掩饰了。
“还跳吗?”李成河问她。
“跳完。”她说。
她们这一组卡司在晏城演了两场,第二场回程的大巴上她一言不发地坐着,低头看手机,聊天记录一直往上滑,除了“早安”“晚安”就是陈若安的一句“我可能要三月份才能回去”。
那时候她说“记得休息”,陈若安也嘱托她,让她别感冒、少受伤、少熬夜……
她没再往上翻,关上手机倚着靠背看外面,她看到一晃一晃的车帘外成群的粉丝,闪光灯星星点点随着人群涌动,车开走了,她把帘子拉了起来。
她一刻不停地审视着自己,找不到犯花,找不到秋女,甚至刨开自己想把小星拉出来,结果谁都只剩碎片。
她不知道究竟哪里改变了,目前似乎没有观众发现,可李成河已经察觉到这些,她觉得观众回过神来只是时间问题。
人真的会经历这样的瓶颈期吗?无缘无故的,在某个短时间的空白期之后就开始破碎,然后再也回不到正轨。她完全想不明白,生平第一次,好像她再也不能说自己懂得舞蹈。
她跟着最早回南安的一拨人回去了,一天又一天,在宽敞明亮的排练室或者冷风习习的阳台,在下着雨的院子里或者空无一人的阁楼,她从没放弃过尝试,或许犯花有时候一闪而过——风穿透她,喝个烂醉然后把阳台的栏杆当成把杆。
她想到就此跳下去的时候,看到犯花向她走来。
还有其他人,很多,她看见穆将军扶着和亲公主下了马车,看见秋女轻拍小星的肩头,月光忽闪嫦娥款款而过,犯花懒懒地拨弄着琴弦,秦淮小调不知从哪里传来。
“去哪了?”她坐下来,醉了还是喝酒,喝到过饱和,“明知道我离不开……一走这么久。”
没人回答。
她笑了,她拎着酒瓶走出阳台,拖着步子走在只有自己的走廊上。
她不知道这些人明天是否还在,不敢抱有期待,其实是期待已经麻木。她不能说自己没思考过这些事的原因,也不能说她真的一点答案都想不到,很多时候是她不愿承认罢了。
是,她早就想到了。
酒瓶放进去,药剂拿出来。
她放在手心里看,然后对着光,白光在玻璃管里被拉扯成各种形状,她转着看,俄文,全不认识。
她放下药了,撕开酒精棉片。衣服褪下一点露出肩头,酒精涂上去,凉丝丝的感觉一圈圈扩大,她安静地做着这些,然后丢了棉片,安静地看着自己。
那一小片皮肤的凉意退去的时候,她知道酒精就要干了。她重新拿起玻璃管来,小小的一支,打开保险盖之后握在手里。
扎下去,尽量快,尽量垂直……
陆望瞻的嘱咐在她脑海中回荡,还有歌声——吴侬软语的小调。
她咬着嘴
第60节(1/2),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。